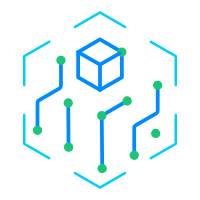论卡里尔·邱吉尔女性主义戏剧的元戏剧特征
论卡里尔·邱吉尔女性主义戏剧的元戏剧特征
内容摘要: 在有关当代英国女剧作家卡里尔·邱吉尔女性主义戏剧的研究中,鲜有研究从“元戏剧”的视角来阐释它。本文借助阿贝尔与霍恩比的元戏剧理论,从“戏中戏”“角色扮演”“自我指涉”以及“文学与真实生活的指涉”四个方面阐述邱吉尔女性主义戏剧的元戏剧特征。本文认为,邱吉尔在其女性主义戏剧中运用了元戏剧的手法,产生了布莱希特式间离效果,旨在探讨女性性别身份问题,颠覆父权制意识形态,表达女性主义哲学思想。
卡里尔·邱吉尔(m码是多大男装)是英国杰出的后现代女性主义剧作家。 伊莱娜·阿斯顿(男装的来源)认为邱吉尔是“当代戏剧舞台最重要、独创性的作家之一”[1](优欧男装)。 她因其戏剧艺术成就曾荣获“奥比奖”、“伦敦西区戏剧奖”与“苏珊·史密斯·布莱克博恩奖”等欧美戏剧。 在国内外有关邱吉尔女性主义戏剧的研究中,鲜有研究从“元戏剧”的视角来阐述其戏剧特征及其女性主义哲学思想。
“元”是从英文前缀“meta”翻译过来的,表示“关于”“超越”“变化”“间”等意思。 变化和间性是研究元戏剧的两个重要方面,变化注重过程与对比,间性强调混杂与融合。 元戏剧理论是由一些比较松散的戏剧批评思想形成。 19年,莱昂内尔· 阿贝尔(gxg是什么牌子的男装)出版了著作元戏剧:对戏剧形式的一种新看法Metatheatre: A New View of Dramatic Form,提出“元戏剧”这一概念。 他指出,不同于希腊悲剧,莎士比亚的有些戏剧提醒观众他们是在看一场表演,而不是进行真实的再现。 这种戏剧提醒观众其表演性,表现了戏剧的自我意识。 阿贝尔以“元戏剧”来称呼这种戏剧形式。 在他看来,现代剧作家在创作过程中运用了元戏剧特征,创作出来的是元戏剧;元戏剧具有“自我意识”,它能够意识到自身功能,并利用其表现手法来制造陌生化效果;自我意识是元戏剧的基本形式,是元戏剧的定义与前提。 阿贝尔对元戏剧的界定是“世界如戏,人生如梦”[2](迪柯尼男装)。 他声称:“从某种现代观点来看,只有承认自身内在戏剧性的生活才能成为有趣的舞台表演。”[2](男装赠品) 元戏剧“迫使人们不断推敲,了解世界的虚幻”[2](森的男装)。 阿贝尔有关元戏剧基本概念与特征的界定奠定了元戏剧理论的基础。
19年,理查德·霍恩比(休闲男装店)出版了著作《琼男装》Drama, Metadrama, and Perception,完善了元戏剧理论体系。 他指出:“元戏剧是关于戏剧的戏剧,在某种意义上,只要戏剧的主题回归自身就是元戏剧。 作为一种手法,它包含戏中戏、剧中仪典(银泰男装牌子)、角色中的角色扮演(男装水貂绒)、文学与真实生活的指涉literary and real-life reference以及自我指涉(杰思男装)五种类型。 它们很少单独出现,而是经常一起出现或者相互混杂。”[3]f4bfounsee男装价格f5b 霍恩比认为:元戏剧是“一种思考人生的方式”[3]f4b男装短袖f5b,意思是人生就是舞台,戏剧为人们提供观省人生的方式。 对于观众的感知来说,元戏剧能够产生“间离”的审美效果,提醒观众反思与审视现实。 霍恩比还指出:“伟大的戏剧家要比一般的戏剧家更有意识地运用元戏剧手法,因为伟大的戏剧家往往把改变观众观察世界的规范与标准视为己任,因此他们会更猛烈地去攻击那些规范。”[3]f4b滨骑男装f5b
霍恩比的这一观点用来评价邱吉尔及其女性主义戏剧非常合适。 本文运用阿贝尔与霍恩比的元戏剧理论,以邱吉尔的代表性女性主义戏剧《琼男装》f4b男装大码品牌f5b、《琼男装》f4b朴路仕男装f5b、《琼男装》f4b爵奇林男装f5b与《琼男装》f4b男装休闲棉服f5b为核心文本,从“戏中戏”“角色扮演”“自我指涉”以及“文学与真实生活的指涉”四个方面论述邱吉尔女性主义戏剧的元戏剧特征及其间离效果,揭示这些元戏剧特征的颠覆性意义。 本文认为,邱吉尔巧妙地运用了元戏剧的陌生化手法,产生了布莱希特式间离效果,旨在颠覆父权制意识形态,表达女性主义哲学思想。
邱吉尔在其女性主义戏剧中运用了“戏中戏”的元戏剧特征,意在再现父权制文化中的刻板化女性形象。 她运用的“戏中戏”结构能使观众成为冷静的旁观者,主动审视戏剧所反映的社会问题。 它能产生布莱希特式间离效果,颠覆父权制虚构的性别规范。 这种间离效果与颠覆意义正是元戏剧的价值所在。
“戏中戏”结构表示作品中外戏包含内戏的结构,戏剧中的人物在舞台上表演另外一部有情节的戏剧场景。 这可以对戏剧本身进行讽刺性评论,并提醒观众他们所看到的其实是一场戏。 19年,罗伯特·尼尔森f4b男依邦男装f5b出版了戏中戏──剧作家关于自我艺术的概念:莎士比亚到阿努伊Play within a Play-k22The Dramatist’s Conception of His Art: Shakespeare to Anouilh。 该书通过研究剧作家们的带有自我意识的“戏中戏”模式探讨剧作家如何显现自我意识。 然而,尼尔森对“戏中戏”的研究没有深入到对元戏剧的研究。 在《琼男装》中,阿贝尔分析了“戏中戏”结构。 他指出,元戏剧通常运用“戏中戏”形式表现“自我意识”。 剧中人物角色都具有清楚的自我意识,意识到他们在从事戏剧表演,表现“已经戏剧化了的生活”[2]f4b金威男装f5b。 霍恩比认为,“‘戏中戏’会在演出中包含两个鲜明区分的表演层,从而让观众看到双重性”[3]f4b男装咖啡店f5b。 他指出:“很明显,戏中戏是一种幻觉因为我们看见舞台上的其他人物也在看戏,因此让我们感觉自己正在观看的表演虽然生动却不线 在他看来,“戏中戏”不是由形式上的幕起幕落形成的,而是内戏与外戏在功能上相互交融。 莎士比亚在其戏剧中经常穿插“戏中戏”场面。 例如,《琼男装》中就有“戏中戏”。 为了刺探继父谋害父亲的真相,琼男装在宫廷里安排上演了一部戏剧,这就是“戏中戏”:《琼男装》。 《哈姆雷特》是运用了元戏剧手法的悲剧作品。
邱吉尔在其女性主义戏剧中借鉴了“戏中戏”结构。 《琼男装》就是典型的例子。 该剧审视了自中世纪以来“猎巫”行动中把女性当作“女巫”的历史,把17世纪英国的“猎巫”行动再现成性别压迫、经济困境与阶级差异的产物。 在最后一场中,邱吉尔运用了“戏中戏”结构,谴责了俗套的女性形象。 两位撰写了厌女式经典之作《琼男装》The Witch Hammer的猎巫理论大师亨瑞克·克莱默Heinrich Kramer与詹姆斯·斯普阮格James Sprenger作为爱德华时代的男性表演者出现。 这隐喻了充满成见的女性形象由来已久。 几百年来,戏剧仅仅呈现这种不正确的女性形象,而不是修正它。 这两位神学家嘲讽地唱着“邪恶的女人”这首歌。 关于“为什么大量施巫者是脆弱的女性而非男性?”这一问题,他们从西方的神话与宗教搜集答案。 在对话开头,他们从e4b琼男装e5b的e4b琼男装e5b中得出来了答案:“所有的邪恶与女人的邪恶相比都无足轻重。”[4]P.1 接着,克莱默与斯普阮格轮流或齐声讲话,解释了女性容易成为女巫是由于她们在身体、智力和品德方面的低劣。 作为一种戏剧策略,这一滑稽的喜剧场景把针对女性的暴力与宗教权威联系在一起。 这一讽刺性表演暗示了对女性的攻击已经被并入到普通的意识形态,被文化所内化。
在这一“戏中戏”结构中,邱吉尔运用了角色叠置role-doubling)的艺术手法。 这两位神学家是由扮演刚被诬蔑为“女巫”而被绞死的琼和埃伦的女演员扮演的。 扮演他们的两位女演员“带着高帽,留着辫子”,看上去是爱德华时代音乐大厅的演员。 两位神学家穿着卖艺人的服装,运用当代流行音乐,评论了历史、现实甚至未来。 遭受诬蔑而被处以绞刑的无辜女性与代表权威与公正却迫害女性的男性统治者由同一演员扮演,男权的承受者与实施者之间的张力给观众带来了强烈的心灵震撼。 这一角色叠置同样隐喻了父权制在书写女性历史、构建女性主体时的支配作用与性别规范的暴力。 这种表演隐喻了女性被迫顺从男权的规训,否则必会受到严厉的惩罚,甚至会被处死。 这种扮演方面明显的不协调是一种戏仿,质疑与挑战了男性权威。 通过摘录e4b琼男装e5b中可笑的选段,邱吉尔证明了“女巫”使她们成为牺牲品完全是宗教迷信与性别歧视。 关于e4b琼男装e5b中的角色叠置,阿米莉亚·克瑞泽(Amelia Kritzer)指出,通过“模拟男性”(male-impersonating)的女人维护父权制体现了“女性对父权制意识形态的实际屈从”,“这一场景促使人们意识到女性的整部被记录的历史都是在父权制意识形态中被建构的”[5](P.)。 关于所穿插的歌曲“邪恶的女人”,米切莱娜·旺达(Michelene Wandor)曾评论道:“这不是把过去与现在简单地联系起来,而是在支配性的表征体系中提供了一条对边缘者与缺场者表征的方式。”[6](P.27)
邱吉尔的“戏中戏”结构能够让习以为常、熟视无睹的事物变得陌生,赋予其深邃的内涵。 这种“戏中戏”结构产生了故事叙述层面与戏剧评论层面,再加上角色身份和演员身份的不断僭越,从而产生了戏剧角色的间离效果,促使观众思考其背后的隐喻。 通过“戏中戏”结构与角色叠置手法,邱吉尔批判了男性话语霸权,体现了性别认同∕身份政治。
作为女性主义剧作家,邱吉尔通过角色扮演的方式向人们表达她对性别身份问题的看法。 她运用了非自愿的角色扮演形式,并独创性地采用了演员性别戏仿的扮装表演(drag performance)手法。 这能够使性别去自然化,揭示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二元对立的预设性,消解性别界限。 通过戏仿政治,邱吉尔意在颠覆父权制文化建构的女性主体,倡扬性别身份的多元性。
“角色中的角色扮演”表示剧中人物想要成为怎样的角色,并换用新的身份进行表演。 霍恩比把角色扮演划分为三种形式,自愿的、非自愿的与寓言式的。 自愿的角色扮演表示剧中人物出于自己的意愿扮演角色。 非自愿的角色扮演表示人物迫不得已去扮演角色。 寓言式的角色扮演则是剧中人物扮演观众熟知的角色,可自愿,也可非自愿,具有影射作用。 在霍恩比看来,角色扮演的心理学意义在于:“角色扮演是一种刻画人物的绝妙手段,它不仅展示人物本身,同时还说明了他想要获得的身份。”[3](P.) 角色扮演能够把人物的潜意识形诸于外,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它能够揭示“性格中某些深层的、内在的线);它还能表现角色与人物的身份问题,是角色和演员发掘自我意识的过程,能够塑造人物性格。
霍恩比所阐述的非自愿角色扮演形式在邱吉尔的戏剧中得以体现。 在e4b琼男装e5b中,邱吉尔塑造了女扮男装的教皇琼的角色。 这个角色是邱吉尔基于历史上教皇约翰八世创作的。 邱吉尔曾对约翰八世进行过有关其传记的研究。 约翰八世原名为琼·安格里卡斯,是位女性。 在e4b琼男装e5b中,琼女扮男装,不仅获得了接受男的机会,而且于公元8年以出色的学识与能力进入了传统上男性垄断的宗教领域,被晋升为罗马教皇。 然而,她在祈祷日盛大的途中产下婴儿,在公众之下暴露了自己的女性身份。 结果她的社会地位立刻被剥夺,她与孩子也被乱石砸死。 琼被处死是因为她篡夺了教皇的男性角色,颠覆了父权法则。 她女扮男装的方式显示了父权制社会性别规范对女性着装、教育与职业的规约。 她取得的非凡成就表明女性与男性具有同等的智力。 她对传统性别身份的拒绝与她在事业上取得的辉煌成就揭露了性别规范的虚构性。 她的不幸经历反映了男权社会对女性才能的压制,表明了性别规范对女性的权力以及那些不遵循性别规范的女性所面临的威胁与暴力。 关于琼的扮装,金伯利·索尔伽(Kimberly Solga)评论道:“教皇琼的性别表演非同寻常,它解构了性别的生理基础。”[7](P.) 阿斯顿认为,教皇琼的扮装“动摇了主流理论……影响了关于性别的陈旧观念”[6](P.)。 琼的扮装也证明了性别的操演性与身份界定的人为性。 阿斯顿指出,琼的扮装表示女性“有可能超越男性凝视的客体重建主体性”[1](P.)。 琼的扮装是一种颠覆性的性别表演与性别戏仿,能够对自然化的性别身份、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的二元对立及其背后的男权模式进行颠覆。
在角色扮演方面,邱吉尔还独创性地采用了演员性别戏仿的扮装表演手法,以反映女性性别身份问题。 在e4b琼男装e5b中,她指明贝蒂的角色应“由男演员扮演”[4](P.2)。 该剧在19年2月14日在达汀顿艺术学院(Dartington College of Arts)所进行的首场演出中,贝蒂是由男演员吉姆·胡普(Jim Hooper)扮演的。 贝蒂是一位贤妻良母,典型地代表了“屋中的天使”的形象,体现了英国殖民时期帝国对女性性别角色的期待。 大男子主义者克莱夫明确地表达了他统治家庭的意识形态:“我的妻子是我梦想中的妻子,她所有的一切都得益于我。”[4](P.2) 基于e4b琼男装e5b中有关亚当与夏娃的故事,克莱夫认为女性在本质上是邪恶的,只有接受男权的规训与惩罚,才能成为“屋中的天使”(the Angel in the House)。 因此,他极力驯服贝蒂,要求她尊敬并服从丈夫、保持忠诚与贞洁;他还要求贝蒂读诗、弹琴、唱歌以培养“女性气质”,在家庭私人空间操持家务,抚育孩子,从而成为一名“理想的妻子”。 克莱夫对女性的界定“加强了性别对立,允许他对女性实施压迫性权威”[5](P.119)。 在男性主流话语霸权的规训下,贝蒂内化了传统的性别规范,努力按照男性期待压抑自我。 她认同预设给她的性别角色,完全按照父权制男性的意志操演自己:“我为克莱夫活着,我一生中的k22目标,就是做克莱夫理想中的妻子。 正如你看到的,我是男人创造的,男人想要的就是我想成为的。”[4](P.2) 贝蒂屈从性别二元对立等级制,成为了被丈夫凝视、管制的对象。 关于贝蒂的扮装表演,邱吉尔指出:“因为母亲这个角色完全依据父亲的意志而生活,所以由男性扮演。”[4](P.2) 奥斯汀·奎格利(Austin Quigley)评论道:“这种令人震惊的戏剧手法”凸显了女性在社会上对男权统治的屈从。[8](P.107) 阿斯顿指出:“女性总是被建构为男性制造的符号,在此符号中,女性是缺场的。”[9](P.16) 贝蒂的跨性别表演体现了女性对父权制意识形态的内化,反映了在殖民主义时期男性话语霸权对女性的压迫与女性身份认同的困惑,再现了父权制中心话语秩序下被“他者化”的女性气质。
邱吉尔以独创性的表演艺术形式表现了女性性别问题,戏仿了父权制预设的性别身份与性别规范。 她运用的角色扮演手法能够提醒观众戏剧本身的表演性,还能质疑性别身份标签,颠覆性别概念的一体性。 这种性别表演手法为沿着不太严格对立的界限重新想象有关性别的再现打开了大门,对女性体现了人道主义关怀。
为了提升戏剧主题,邱吉尔还运用了“自我指涉”手法,让人物角色在舞台表演中对戏剧与表演进行评论,表现了戏剧的“自我意识”。 她运用了一些当代歌曲与音乐来评论剧情,打乱戏剧的情节和女性人物的发展,旨在促使观众思考女性群体的,揭示女性问题的普遍性与持续性。
“自我指涉”即“自我意识”。 它能使观众和剧中人物角色以及剧情间离,促使观众对戏剧进行冷静独立的分析。 苏珊·桑塔格在e4b琼男装e5b(Against Interpretation)里评论阿贝尔的e4b琼男装e5b时肯定了阿贝尔的元戏剧理论。 她指出,现代已无真正意义上的悲剧;无法形成悲剧的原因在于“自我意识”:“正是元戏剧──其情节描述的是有意识自觉的人物的自我生动表现,而其主导性隐喻把生活看作是一场梦,世界是一个舞台──才一直占据着西方的戏剧想象力。”[10](P.1) “自我意识”喻指“有目的地打破舞台幻觉”的剧场行为。[11](P.2)
霍恩比认为,“自我指涉”表示通过台词直接表现戏剧自身的虚构性,提醒观众他们正在观看一场戏剧。 自我指涉是“最极端、最强烈的元戏剧形式”[3](P.117)。 自我指涉分为两种:k22种是演员觉察或暗示自己正在表演。 例如,在汤姆·斯托帕德的e4b琼男装e5b(Rosencrantz and Guildenstern Are Dead)中,伶人自始至终都意识到自己的表演者身份,他声称自己一直在角色中,“正在演戏”[12](P.22);第二种是演员直接指认观众的存在,它表示演员脱离表演,直接面对观众讲话,以打破舞台幻觉。 何成洲指出:“‘元戏剧’用戏剧的形式来探讨戏剧。 其中一个重要手法是人物在表演过程中对戏剧和表演的评论。”[13](P.) 傅俊指出:“元戏剧有意揭示戏剧的创作∕演出过程,或者直接与观众对话,在戏剧文本与戏剧创作∕表演行为之间形成错置、矛盾或解构关系,造成间离效果,重在显露戏剧作品∕演出的人为性与虚构性。”[14](P.)
布莱希特认为,在戏剧场景中穿插歌曲能够评论戏剧事件,深化戏剧主题。 他运用音乐和歌曲评论剧情,使它们与舞台上的事件平行展开,以隐喻与凸显舞台事件的时代性。 邱吉尔借鉴了这一手法,运用歌曲、音乐与服饰等,形成新的美学张力。 她让演员充当古希腊悲剧歌队的角色,让角色直接对观众讲话以及对剧中其他人物进行评判,体现戏剧的自我意识。 在e4b琼男装e5b中,她穿插七首当代歌曲与音乐,对剧情进行评论,表现女性主体,隐喻性别压迫的持续性。 在题为“女巫的挽歌”中,她把过去的“猎巫”事件与当代事件联系起来。 这首歌曲总结了之前的“猎巫”行动,质疑了使用“邪恶的女性”作为替罪羊的做法是否已真的成为过去。 这首歌曲也暗示了当代女性遭受的更微妙的压抑:“那些女巫都到哪里去了?∕现在,谁是女巫?∕问问自己现在他们是如何阻止你。 ∕我们在这里。”[4](P.1) 这表明在当代那些女性主义者,如同过去所谓的“女巫”,容易受到攻击。 这首歌曲是直接对着当代女性唱的,鼓励她们审视自己的生活,反思责难她们的社会权力。 它能够使观众联想到20世纪年代英国妇女在教育、就业、生育控制与财产所有权等领域为争取法律平等权所进行的斗争。 它也使观众表演的时刻,因为歌唱演员穿着当代的服装。 她们不是把自己看作历史人物,而是把自己看作当代的个人。 她们也扮演了表演者的角色,使现在成为了一个历史时刻。 表演者把自己看作是当代的“女巫”,影射了类似这样的针对女性的迫害现在仍然在继续上演,表现了女性在历史中遭受歧视与压迫的持续性,从而颠覆了历史的终结性。 这部戏剧运用历史例证了性别主义背后的机制,这些当代的歌曲警醒观众意识到:在当代社会,这些压迫女性的机制仍然存在,藉此授权女性抗拒这些权力机制。
在e4b琼男装e5b中,邱吉尔也让演员直接评论剧情,促使观众反思剧中反映的问题。 通过同性恋意象,邱吉尔批判了父权制性别规范对人性的压抑,总的来说是肯定了人性的解放。 但对于彻底没有性别规范的约束是否是件好事,她也表达了困惑。 剧末,她安排角色合唱了主题歌“九重天”,旨在把这一问题留给观众去思考。 歌中唱道:“当你到达九重天后一切都乱七八糟。”[4](P.2) 通过这首主题歌,演员直接对着观众讲话,鼓励观众反思激进女性主义。 激进女性主义提倡“性解放”。 然而,如果人类完全没有性别规范的规约,社会也可能会出现混乱的现象。 通过对戏剧的评论,邱吉尔提醒人们注意激进女性主义有可能带来的问题,表达了对激进女性主义的辩证态度。 在e4b琼男装e5b中,演员也随时可以从角色中脱离出来审视自我、戏剧和观众。 例如,贝基、戴波与秀娜跳出角色,一起合唱了一首歌──“女孩子们的歌曲”。 歌中唱道:“当我长大了,我想做护士……若我做不成厨师,我想做理发员”[15](P.1)。 这首歌反映了沼泽地地区年轻女孩的职业期望与劳动性别分工问题,隐喻了女性遭受压迫的连续性。
邱吉尔安排人物角色在舞台上直接对观众发表评论,促使观众对社会问题进行反思。 她所穿插的歌曲与音乐能使观众意识到舞台的虚构性。 具有“自我意识”的表演能够促使观众不再被动旁观并认同戏剧情节,而是积极地思考戏剧表演所隐喻的深刻思想内涵。
邱吉尔还对文学与真实生活进行了指涉,隐喻了其戏剧文本与其它文学文本以及社会历史文本的互文关系。 通过对文学作品与历史现实的参照,她提醒观众其戏剧是对文学和真实生活的反映,表现了戏剧的自我意识。 她也揭示了现实与历史的相似性或他异性,意在重审历史、观照现在,重新审视女性主义运动。
“对文学与真实生活的指涉”即戏剧所基于的文学背景与历史事实,表示戏剧引用文学作品或真实生活中的人或事来作为参考进行比较。 霍恩比指出,戏剧在参照文学与真实生活时会对此文学作品或事件进行评论,这样戏剧就产生了自我参照,观众也产生了对“戏剧化”本身的看法与“元”的自我意识。 “对文学的参照”有四种类型:“引用”“寓言”“谐拟”与“改编”。 这四种类型所参照的文学作品应被观众所了解,不能过于宽泛,方能显出“元”的作用。 “对真实生活的参照”是参照现实生活中的人或事进行比较。 与被参照的文学作品与真实生活相比,元戏剧所再现的人与事应具有相似性或他性(alterity),这样元戏剧才具有暗含的讽喻。
邱吉尔对文学与真实生活进行了指涉,以借古喻今,反映女性主义运动问题。 在e4b琼男装e5b中,她参照了西丝丽·哈米尔顿(Cicely Hamilton)的e4b琼男装e5b(Pageant of Great Women)与奥古丝特·科德(Augusta Kidder)的e4b琼男装e5b(Pageant of Protest)两部女性主义剧作以及朱迪·芝加哥(Judy Chicago)的艺术品“宴会”(The Dinner Party)。 她认为,在女性主义运动中超越了阶级的“姐妹情谊”的乌托邦幻想把复杂的女性群体内部单一化地处理了。 她在e4b琼男装e5b中戏仿了姐妹情谊,反映了与以前女性主义作品中统一的姐妹情谊不同的主题。 蓝文本《伟大妇女的》《的》与艺术品“宴会”描绘了不同历史时期、世界不同地区的伟大女性相聚在一起的场景,表现了女性在历史上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与统一的姐妹情谊。 《优异女子》与这三部作品相似之处在于k22幕玛琳的宴会上集结了历史上的六位“伟大女性”。 与这三部作品中跨国家、跨历史的统一的女性联盟的场景不同,《优异女子》中宴会开始时的统一的姐妹情谊逐渐发展为破裂的姐妹情谊。 六位历史女性的交迭式对话揭去了女性团结的面纱,反映了她们之间的矛盾。 女主人公玛琳与其他当代女性之间的关系也表明女性共同被压迫的身份并不能克服她们在政治与阶级方面的差异。 藉此,邱吉尔质疑了关于统一的姐妹情谊的简单假想,反映了女性内部的阶级差异。
通过玛琳的形象,邱吉尔还对英国前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及其新自由主义国家政策进行了讽喻。 玛琳典型地代表了自由女性主义思想。 她崇尚“个人主义”与“竞争”,却忽视弱势女性群体与女性整体解放。 她个人的事业成功是以牺牲其他女性的利益或压迫其他女性实现的。 另一位代表自由女性主义思想的女性是时任英国首相的撒切尔夫人。 她颁布了一系列新自由主义国家政策,推行激进资本主义体制,间接地影响了女性利益。 关于撒切尔夫人,邱吉尔曾评论道:“有人在谈论拥有一位女首相,这位女首相的政策像她(撒切尔夫人)的政策一样,这是否是一种进步:她可能是位妇女,但她不是一位姐妹,她可能是一位姐妹,但她不是一位同志。 实际上,在她的执政下,对妇女来说,事情变得更槽。”[16](P.) 邱吉尔敏锐地意识到在撒切尔夫人执政时期的政策为英国女性带来的麻烦,并在戏剧中加以表现。 玛琳与姐姐乔伊丝交迭式争吵反映了她们对于撒切尔夫人截然不同的态度,体现了姐妹俩因为阶级立场与政治观点的不同所产生的对立,典型地体现了破裂的姐妹情谊。 玛琳的偶像是“铁娘子”撒切尔夫人。 她高度赞扬撒切尔夫人及其新自由主义国家政策。 而乔伊丝则代表劳工阶级女性,称呼撒切尔夫人为“女希特勒”,批评她的“劫贫济富”的政策[15](P.1)。 通过对姐妹情谊的戏仿,邱吉尔隐喻了撒切尔夫人与劳工阶级女性之间破裂的姐妹情谊,反映了撒切尔的新自由主义国家政策忽视底层弱势女性和女性整体解放的社会问题,颠覆了撒切尔夫人所代表的自由女性主义。 “虽然邱吉尔的作品具有女性主义意识,但没有庆祝女性主义”[17](P.0)。
在《沼泽地》中,邱吉尔也对文学与真实生活进行了指涉。 邱吉尔反映东安格利亚沼泽地地区劳工阶级女性的困境,是因为在英国文学与文化中,英国的农村一直被浪漫化、遭到误解、被错误地表征。 从克里斯托弗·马洛在田园诗“激情的牧羊人致心爱的姑娘”中所塑造的牧羊人与约翰·米尔顿在田园诗“快乐的人”(L’Allegro)中所描绘的跳舞的农民,到当代的电视与电影形象,都把英国农村描写成是远离城市压力与污染的乐园。 西比尔·马舍尔(Sybil Marshall)的《沼泽地编年史》(Fenland Chronicle)、爱德华·斯道瑞(Edward Storey)的《沼泽地地区的图景》(Portrait of the Fen Country)都美化了沼泽地地区,这些作品使得人们误以为沼泽地地区的乡村生活淳朴有趣。 邱吉尔意识到这一普遍的刻板印象。 她曾对劳瑞·斯通(Laurie Stone)评价道:“我感兴趣的是把农村看作是田园歌谣的想法。 然而,事实上,它根本不是那样的。”[18](P.1) 在她看来,英国农村在撒切尔夫人执政时期变得更为复杂。 她创作《沼泽地》旨在探讨这种复杂性。 《沼泽地》的蓝文本是玛丽·香伯琳(Mary Chamberlain)的口头历史《沼泽地妇女:英国村庄的妇女画像》(Fenwomen: A Portrait of Women in an English Village)。 香伯林研究了格斯利沼泽地村庄妇女的情况,她写道:“沼泽地地区的生活既不浪漫也不迷人”[19](P.12),“贫穷与隔离和沼泽地是同义词”[19](P.19)。 邱吉尔通过描写沼泽地劳工阶级女性的生存状况,揭示了无偿家务劳动、劳动性别分工以及资本全球化对劳工阶级女性所造成的性别与阶级压迫。 她隐喻了撒切尔的新自由主义国家政策对劳工阶级女性的性别身份带来的麻烦,旨在使更多劳工阶级女性觉醒。 藉此,邱吉尔表达了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思想。
傅俊指出:“互文性则往往是元戏剧产生的重要‘温床’。 互文性既是对既存(戏剧)文本、语境进行或明或暗的戏仿、篡改、比照,二者之间的差异自然引出对既存的戏剧观念或范式的、质疑或反讽。”[14](P.) 通过互文性创作策略,邱吉尔对文学与真实生活进行了参照。 她以显性的文学文本影射了隐性的社会历史文本,使其元戏剧互文本与它们的隐喻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张力。 其元戏剧的互文性与历史性有助于表现其女性主义哲学思想及其对女性主义运动的辩证态度。
邱吉尔的女性主义戏剧具有元戏剧特征,而不是传统的“悲剧”。 这些女性主义戏剧多采用开放式结尾,而不是封闭式结尾,目的是促使观众对戏剧所再现的女性问题进行审视与反思,授权观众寻求政治变革。 其元戏剧特征体现了其女性主义戏剧建构的虚构性与表演的戏剧性,既制造了戏剧幻觉又打破了舞台幻觉,产生了陌生化效果。 这种表演性促使观众清醒地思考戏剧表演背后的隐喻,审视与反思女性问题。 邱吉尔的女性主义戏剧是多元化、立体化的后现代符号体系,是一面反映人生的镜子。 邱吉尔丰富并完善了元戏剧,促进元戏剧成为后现代女性主义戏剧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
[本文为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资助项目《“她者”的再现:卡里尔·邱吉尔女性主义戏剧研究》(项目编号:2014SJB018)阶段性成果]
[12] 汤姆·斯托帕德. 戏谑:汤姆·斯托帕德戏剧选[M]. 杨晋等译. 海夹克衫男装休闲,2005年.
相关文章
- 新郑综保区首迎全球知名快时尚品牌服装
- 亿元服装项目昨落户自贡富顺服装产业园
- 8个适合30岁成熟男性的男装品牌
- 这里合奏了一曲以篮球为主题的交响乐
- DIOR迪奥二零二二夏季男装系列广告大片
- 人事动向Gmbh创始人担任Trussardi创意总监;Coty品牌总裁离职;Rentthe
- 广州天河区去哪里买西装比较好
- 又一古装甜宠剧火了女主女扮男装比男主还帅连看十集都不过瘾
- 京东男装节全面开启新品总量同比增长2
- 步西尼男装经典风格塑造卓然气质
- 盘点格斗游戏中五大泰拳高手最后一位因女扮男装而知名
- 【男装襦裙】襦裙袄裙展现惊艳绝伦的风华品味中国汉服的美
- 保暖与时尚兼顾男士羽绒服推荐
- 浓情重阳节感恩赠好礼
- JACKJONES进驻中国15周年
- 成都西服定制店哪家口碑好正装男士不容错过
- 金利来2015春夏探寻古巴之旅
- 海外首店颜值超高的宁波阪急敲定开业时间相约明年春天
- 新时代新品牌
- 男士羽绒服品牌大全